第三百四十八章 餐前甜点
夜红绫语气淡淡:“你负责暖床就行。”
绫墨眉目低敛,温顺而乖巧:“暖床的意思其实就是侍寝。”
“暖床的意思是暖被窝。”夜红绫平静地道,“你自己说的,到了寒冬腊月就可以做得很好。现在还没到寒冬腊月,但本宫同意让你先学。”
绫墨撇嘴:“我想侍寝。”
夜红绫瞥他一眼:“恃宠生骄?”
身段颀长容色俊美的青年沉默片刻,抬起眸子定定地看着她,眼底有深邃的光芒涌动。
他不说话,就这么看着她。
夜红绫面无表情。
绫墨唇角微勾,忽然间一个饿狼扑羊似的动作,凶狠地把夜红绫压倒在床榻上,低头吻住了她柔软清凉的唇瓣。
四目相对,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这个时候大概也无人还有心情去思考什么权谋,连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都是多余,夜红绫没有抗拒他的动作,分别一月有余,思念的人不只是他,她也挺想他的。
兴许是因为她默许的态度,青年表达感情的方式凶狠而野蛮,只带着一种恨不能把她生吞入腹的霸道,尽情地发泄着自己的思念和柔情。
夜红绫虽不怎么擅长回应这种,却由着他,唇瓣被蹂躏得生疼酥麻也没有抗拒。
可这个人就像是一匹饿狼似的,浑身都散发出想要吃肉的冲动,动作越来越野蛮凶狠,原本一只手托着她肩膀,另一只手握着她纤细的腰身,慢慢的,两只手同时去解她的衣袍......
夜红绫皱了皱眉,抬手探向他的脑后,抓住他的头发并微微使力,迫使他抬头。
头皮传来的疼痛让绫墨清醒了片刻,动作微顿,随即茫然地直起身子,不解地看着被他压在身上的女子。
依然是四目相对。
夜红绫眼神一片清明,而绫墨沾染了情欲的瞳眸却是一点点恢复了清明。
目光触及红肿的唇瓣,绫墨诡异地沉默片刻,随即默默抬眼看着夜红绫,眼神里透着几分心虚,以及几分心疼。
修长手指抚过她的唇瓣,绫墨复又埋下头,把脑袋埋在她的肩颈当鸵鸟。
良久都没说话,就这么静静躺了一会儿。
“我做主人的驸马好不好?”
青年低声软糯地开口,嗓音里透着让人不忍拒绝的希冀和某种难以言说的渴望。
夜红绫语气淡定:“不是男宠吗?”
“男宠若是可以侍寝的话,我当然没什么意见。”青年语气里多了丝哀怨,“可主人总是不让我侍寝。”
夜红绫默了一阵,淡淡道:“没说不让。”
他身强力壮,对她又是一腔刻骨柔情,自然避免不了某些方面的想望,而她也十七岁了。
寻常人家的女子十五六岁就嫁人,嫁人之后自然就要面对夫妻之间的私密之事,甚至十六七岁就生孩子的也比比皆是。
所以年龄上也没什么需要顾忌的。
至于名分......
夜红绫更不在意这个,连侧夫都一个个纳进了府里,还在乎什么名声闺誉?
所以,为什么不让他侍寝?
似乎没有非拒绝不可的理由。
这句话闪过脑海,她眉头拧了拧:“你真想侍寝?”
绫墨一听有戏,顿时来了精神,从她脖颈里抬起头来,双眼亮晶晶地看着她。
夜红绫嘴角抽了抽,淡淡道:“本宫倒也没什么不愿意......”
“主人是想选个良辰吉日?”绫墨眉眼弯了弯,从善如流地接口,嗓音渐渐染上了蛊惑意味,“我觉得侍寝这种事情本身是美好的,让人憧憬的,所以的确该选个好日子......嗯,先一起洗个鸳鸯浴,水面上撒些花瓣,洗得香喷喷的,温言软语一番,气氛正浓,水到渠成......”
夜红绫没什么表情地看着他,听他说得自我陶醉,抬手敲了敲他的脑门。
“择日不如撞日。”
啥?
绫墨呆住,随即眨眼看着夜红绫:“主人的意思是......”
夜红绫没说话。
绫墨深深吸了口气,压下心头躁动,低头吻着她红艳艳的唇瓣,嗓音带着压抑的情动,“主人今晚累了,早些睡吧。”
夜红绫闻言,不免就有些意外:“你能忍住?”
她几乎可以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
绫墨露出一副委屈的模样:“不能忍也得忍。”
他想让两人的第一次发生得美好甜蜜,让她刻骨铭心,一辈子都忘不了。
不过。
他想了想,虽然那种事情男人天生擅长,但他是不是应该去找本册子学习一下?免得因技术生疏而留下什么不美好的回忆。
夜红绫不知道这人心里的想法,见他能忍也就没再多说什么,淡道:“睡觉吧。”
绫墨还在想该以怎样的方式把他家可口的主人慢慢吃干抹净,闻言却立即回神,伸手把夜红绫身上的袍子解下,起身挂在檀木衣架上,然后利落地脱掉自己身上的外袍一同挂上
转头看到床上的夜红绫已经掀开被子躺了进去,绫墨一溜烟钻进了被窝,无比熟练地占领领地。
“主人......”一手把她揽进臂弯,小狼狗再次埋脸在她颈侧轻啃,“主人的肌肤好细腻。”
夜红绫被他又亲又啃,弄得脖子痒痒的,不由伸手推开他的脑袋:“安分一点。”
这是两人分开之后第一次同床共枕,绫墨能安分才怪了,而且主人亲口应允择日不如撞日,虽然尚未发生亲密的事情,但无形中却是让两人的关系有了更实质一点的进步,他当然要趁着这个机会这样那样了。
安分?
不存在的。
在发生更深一层的关系之前,总忍不住先尝尝饭前甜点的美味。
这一夜就在蠢蠢欲动的甜蜜中过去。
而公主府地牢里,有个人却忍受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
寒玉锦做了个离奇的梦,梦中发生的一切让他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和呻吟,涔涔冷汗从各个毛孔里溢出来,重重衣衫尽湿,惨白的脸上尽是惊惶未定和不敢置信的恐惧。
凌迟之痛,痛得他脸色扭曲,深陷噩梦中迟迟无法醒来,清醒而又虚幻地承受着酷刑的折磨。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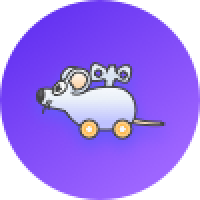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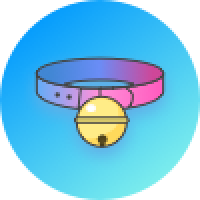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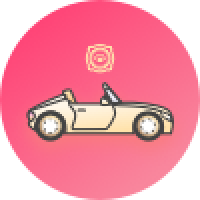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