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六章 罪罚
张正信点头:“确有此事。”
陈兴德听的脸皮子直抽搐,手指颤颤巍巍指着梁十七,一口气不上不下:“你,一本假菜谱你们报什么官?”
你特么一本假菜谱丢了就丢了,何必搞得一副天快要塌下来的样子!
起初,陈兴德拿到辛飞偷来的菜谱也曾怀疑过其真假,怕梁十七将计就计弄一本西贝货骗他,直到眼线来报,说崔钰焦急地去报官,他才断定菜谱是真,感情,这一切都是梁十七设下的局,一个个都在演呢?!
陈兴德真想一口老血喷出来。
他千防万防,自以为足够小心,却还是被梁十七套路了。
梁十七转过头,无辜地看着他:“陈老板,咱说话能不能讲点道理,菜谱真的也好,假的也罢,总归是我们客来轩的东西,人家大马路上丢三个铜板都有报官的权利,丢一本菜谱咋就不能报官了?再说了,正是因为菜谱内容是错的,我们才着急啊,就怕被有心人士利用,一不小心就害了无辜百姓,您瞧,泰和楼不就是一个例子么。”
“我撬你个仙人板板!你个小贱人玩我,我呸!大人,你可听见了,她亲口承认菜谱有问题,要不是她设计想陷害我,那些百姓也不用遭受折磨,这一切,都是梁十七的阴谋!”陈兴德已经失去了理智,气到口不择言,他瞪大眼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要不是手脚还戴着镣铐,都想扑上去咬死梁十七。
“搞笑,照你这说法,用刀杀人,就抓铸刀师,被砒霜毒死的,就抓卖砒霜的老板,官府还查什么案抓什么杀人凶手?”
“你......”
“我什么?你不偷菜谱屁事没有,泰和楼没本事跟客来轩正面交锋,却在背地里下黑手,说白了就是你陈老板贪心不足蛇吞象,既想要赚钱又想要落个好名声,可世上怎么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陈老板一个人独占,我客来轩做生意,一步一个脚印,马大厨做的神仙鸭也好芙蓉海蚌也罢,都是经过无数次改良才得到的菜谱,你偷捡着去用还倒打一耙,你要脸吗?”
就是,要脸吗!
外头的百姓也附和,就像梁十七所说,不偷就啥事没有,自个儿犯贱要去当贼,偷了人家的宝贝又嫌宝贝是假的,让苦主赔偿,所以,好坏全凭你一人说了算呗!
咋不见客来轩吃坏人呢?
当然,林奎闹事那次不算,那是没事找事。
总得来说,这个偷盗案件案情十分明朗,尽管陈兴德颠三倒四磨破了嘴皮子想把黑锅扣梁十七头上,那也得看梁十七愿不愿意背,百姓不聋不瞎,张正信也不是个昏官。
但难就难在菜谱的价值该如何衡量。
根据大周朝的律例:诸位盗窃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得财,盗窃罪均成立,鞭笞五十下,财物价值一尺绢的杖六十,每价值多一匹罪罚就加一等,到五匹绢的价徒刑一年,每增五匹罪罚加一等,如果盗窃价值满五十匹就处以役流,而实际上,通常满四十匹就会被流放三千里。
盗窃没有死罪,强盗才有死罪。
盗窃转为强盗罪那又是另一种说法,暂且不提。
再说说共同盗窃,即两个人及以上的共同实施盗窃的行为,眼下陈兴德和辛飞便是属于共同盗窃。
对此,大周也有律例:诸共盗者,并脏论。
只要有一个人盗窃得手,所有人均按盗窃罪论处,也就是说,陈兴德和辛飞甭管谁主谋谁从犯,罪责都一样,马永宁算不算在其中要看张正信如何判断,毕竟陈兴德这只疯狗急了谁都要咬,他巴不得多拖几个人下水,马永宁只能证明没有闲暇去偷窃,却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参与。
有没有偷盗还不是张正信一句话的事情,更遑论他之前还有案底。
马永宁跪在一边,两股颤颤,吓得面无血色。
辛飞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到不担心坐牢,区区牢锁,空手派的弟子难道还开不了?他怕的是挨鞭子,官府的鞭子可不怎么软,五十鞭下去,不死也要脱层皮。
早知道杨鸿云身边有轻功高手,他何必为了五十两银子赶这趟浑水,活着不好吗?
色字头上一把刀,贪字头上两把刀。
经过这遭,辛飞都有点想金盆洗手不干了!
去他娘的江湖,去他娘的江南富商人傻钱多,一个个都跟猴精似的,又抠又精,尤其是女商人,套路一层一层,比千层酥还多。
如果能刨开辛飞的肚子,此刻他里面的肠子肯定是青色的。
梁十七哪里知道辛飞在想什么,硬邦邦的青石地板,她跪的膝盖有点疼,偏生张正信皱着眉头在思忖,她也不好出声打搅。
按理说这案子很好判,陈兴德和辛飞左右都逃不掉五十鞭,就是后面的刑罚不太好判,判太轻,泰和楼仗着梁十七的菜谱卖神仙鸭一百二十文一只,芙蓉河蚌九十五文一盘,三天少说赚了二十两有余,按绢布十文一尺四百文一匹来算,都能判役流了,但倘若判役流,菜谱本身的价值就值几十文钱,也就是六十杖。
张正信有点头痛。
于是,他选了个折中的法子,惊堂木一拍:“犯人陈兴德、辛飞,盗窃他人财物,鞭笞五十,外加徒刑一年;马永宁知情不报,以盗窃罪同论,鞭笞五十,另,泰和楼菜品有异疑似掺毒,即日起关闭封查清理。”
“来人,即刻行刑!”
陈兴德等人面如死灰,衙役将他们拖到门口行刑。
梁十七不想看到太过血腥的场面,她退到一边,跟杨鸿云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县衙。
崔桓没来,听林阳泽说他最近老毛病又犯了,没怎么去上课,崔钰好几天没见着他,一听就急了,立马赶着马车回崔府。
梁十七和杨鸿云自然也要去探望,至于菜谱,等案子结束后再来取也不迟。
路上,崔钰还很奇怪地问杨鸿云:“我哥每天都要去书院上课,你和林阳泽怎么那么闲?”
林阳泽至少有理由,毕竟人家家务事繁忙,休妻后心情需要缓缓,可杨鸿云什么情况?整天在客栈待着,崔钰掰起手指算了算,他都有半个月没去上课了,该不会被学院开除了吧?
杨鸿云低头沉默片刻,撇了下嘴:“啧,天太热,不想去。”
崔钰仿佛见鬼:“你刚才啧了一下,你居然因为天气太热嫌弃书堂?被夫子听到你就完了。”
杨鸿云用看傻子的眼神看崔钰,解释道:“我入学是五月,按理,五月是田假,有一个月休沐,不过万里书院学生少,且都在本地家境还不错,没有学生要返乡种田,书院便将田假取消,转而挪到七月。”
院长此行也是不得已为之,江南地带夏季多闷热,白天太阳一晒,学堂里热的要命,若是碰到雷雨天气更惨,坐在学堂里就跟坐蒸笼里一样,夫子讲课,没多久便汗流浃背,学生年轻体健还能忍一忍,可怜那几个年长的夫子,轮着中暑。
上次杨鸿云他们去郊外也是因为学堂里太热,他们又不像客来轩财大气粗能四处摆冰盆,只好去阴凉的山林水涧或者山洞里上课。
但去郊外路途遥远,而且地方也不好找。
常言道,书生大多手无缚鸡之力,这般连续来回走上几天,学生也受不了,还特浪费时间。
院长愁啊,夫子病倒了,要是学生再倒下,他这书院也不用办了,于是他脑门一拍,索性给大伙放假,让他们自个儿回家读书去。
而崔桓身子弱,本就娇气,在家冰盆摆满,还有丫鬟小厮扇扇子伺候,他在学堂里坚持了几天,这不就中暑了嘛!
崔钰回到家,就看到崔桓病恹恹地躺在榻上,有气无力的,他的书童言儿正在一旁扇风。
“大哥,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言儿,请大夫了吗?”崔钰跪坐在榻边,眉宇间满是担忧焦虑。
言儿一板一眼道:“回二少爷的话,已经请大夫看过了,大夫说,大少爷是中暍,给开了药,卧床数日好好休息便能无事。”
他没敢说崔桓被抬回来的时候四肢湿冷,呕吐了好几次,脸色白得透明,仿佛风一吹人就没了,那时候他真的被崔桓吓得不轻,只是崔桓千叮咛万嘱咐,不可将此事告知崔钰。
二少爷的性子他也知道,他在外人面前收敛起所有锋芒,圆滑却不世故,有时候还傻得可爱,可在高门贵族里长大的爷,哪能真的纯善,事关大少爷,二少爷就会变成最锋利的那把剑,见谁砍谁,就像之前府里的那些厨子和厨娘,二少爷不过是偶然听到他们在背后嚼舌根说了大少爷一句,便大发雷霆,越过大少爷直接将他们杖毙。
主子打杀奴才不是什么大事,阳奉阴违吃里扒外就该死,但大少爷不愿二少爷手染鲜血。
杀的人多了,心会染黑。
这次大少爷中暍,是他和几个丫鬟伺候不周,二少爷知晓定然要拿他们立规矩,大少爷不愿说,也是想保他们。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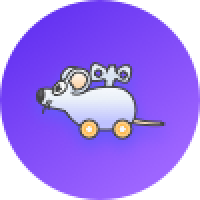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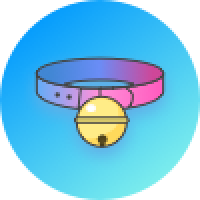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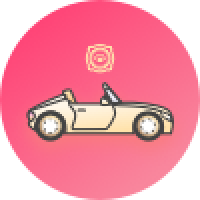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