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出狱
崔钰没听出崔桓语气有异,还颇为理解地点点头:“我起初听到也吓了一跳。”
崔桓转过身时,脸上已经看不出异样,他唤来奴仆清扫地上的瓷片,坐下问:“那你可有劝他?”
崔钰撇嘴:“劝了,他不听。”
崔桓坐下笑道:“他与祖父性格最是相似,一旦做了决定,那便再无转圜之地,若是能劝说得动,当初祖父也不会被贬谪二十载。”
不过杨鸿云与崔文学也有不同的地方,崔文学太过正直,眼里容不下沙子,所以经常被政敌攻讦,但杨鸿云不一样,他的心思更难以捉摸,面具戴久了,有时候崔桓都分不清到底哪一面才是真正的他。
“大哥?”崔钰叫了崔桓好几声都未能回应,只得伸手推他。
崔桓回过神:“嗯?”
“我刚才说想替他先瞒着祖父,你怎么看?”
“这个么......”崔桓眯起眼,屈指一下下敲打在桌面上,他沉吟许久,开口道,“既然如此,那便先瞒着吧。”
“行。”
崔钰离开后,书童言儿端来一碗褐色药汁,垂首往上托:“少爷,该喝药了。”
崔桓端起那碗药,看到药汤里倒映出自己的影子,他忽然唇角一勾,抬手就把药汁泼到窗外,嗓音带笑道:“言儿,从今日起,不必再熬药了。”
言儿稚嫩的小脸上没有一丝惊讶和疑惑,像个木偶般面无表情地应道:“是。”
杨鸿云,这盘棋,你我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这天晚上,注定不平静,就在崔钰呼呼大睡的时候,崔府灯火透明,管家带人将整个崔府清洗了一遍,手起刀落,崔府上空血雾漫天,崔桓披着黑色斗篷站在屋檐下,面冠如玉,他明明唇角带笑,但眼神却如同锋利的刀子一般,看着台下跪俯的一干人奴仆,以及他们旁边的一具具尸体。
到了这时候,那些被崔夫人派过来的眼线才明白过来,和二少爷比,这位才是真正的狠角色,他们到死前咽下最后一口气,也想不明白,他们的身份究竟是何时暴.露的?
月色皎洁如霜,空荡的牢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杨鸿云所在的牢门锁链被打开,一个墨衣锦袍的男子跨入牢中:“我们又见面了。”
杨鸿云看向他,凤眼中眸光微闪。
与此同时,躺在床上的梁十七浑身发烫,昏睡不醒,卢翠桃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顾男女大防,连夜去敲李大仁的屋门,带着哭腔道:“十七烧得厉害,求你帮帮忙!”
李大仁一听哪敢耽搁,赶紧叫杨松起来,把梁十七背上马车,赶去石门镇益仁堂找徐大夫。
徐大夫坐在凳子上给梁十七搭脉,只见原本丰.腴肥胖的梁十七,如今嘴唇苍白地躺在床上,面颊上浮起两片不自然的红晕。
徐大夫用手背贴了下额头,烫得吓人:“她是何时开始发烧的?”
卢翠桃在一旁抹眼泪,自责道:“我发现是在酉时,但申时之前她就不大有精神,我以为她是忧虑她家相公,就没有多想,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她都病了还给我们做饭,都怪我太粗心,都没能能早点发现。”
“那之前可有受过寒?”
“有有有,大概五天前,她落过水。”杨松也面露愧疚,自从杨鸿云出事后,梁十七一直在忙碌奔波,他们却从没有真正关心过她,连她病了都无人察觉。
“大夫,我儿媳的病严重吗?”
徐大夫打开药箱,取出里头的针包,给梁十七捻针:“她之前落水寒气入体,没有好好休养落下了病根,这几天又劳累过度,再加上她郁结在心,大抵昨夜又吹风着了凉,这一件件加起来,铁打的身体也经不起她折腾。”
杨松心中一惊,忙问道:“那该如何是好啊?”
“倒也不必太过忧心。”徐大夫手上有条不紊地扎针,慢吞吞道,“待会我开两个方子,待热症压下去后,再服用另一贴药调理身子,不出半个月便能痊愈。女子最忌体虚体寒,她年纪轻轻往后若是想要有子嗣,可不能再如此随意了。”
“是是。”杨松连连应道。
他付了诊金,卢翠桃拿方子去抓药。
待药熬好后,徐大夫将银针依次取下,梁十七悠悠的睁开眼,她感觉头昏脑涨,视线有些模糊:“我这是在哪儿?”她该不会又穿了吧?
卢翠桃面露惊喜:“十七,你醒了!”
梁十七偏过头看她,心中不知是喜是悲,原来她还在古代。
卢翠桃扶着她的肩膀让她坐起,往她身后垫了两个软枕,端过药给她:“徐大夫说你喝了药就会好,慢点,小心烫。”
“多谢。”梁十七嗓音沙哑得厉害,一开口就跟针扎似的疼,她接过药碗,仰头一饮而尽,药里不知道放了多少黄连,苦得她差点落下泪来。
这次,连个给她送糖的人都没了。
梁十七嘴里泛着苦味,一直苦到心里,她闭上眼,病恹恹的连句话也不想说。
这时,门外的布帘忽然被撩起,卢翠桃和杨松见到来人,脸上满是不可思议,还有几分惊喜。
梁十七听到门外的动静,但没睁开眼,她嘴里苦的要命,心情也不大好,心道,不管是谁来,她都没心思应付,反正天大地大病人最大。
这般想着,嘴里却被塞进了一块蜜.汁锅炸,外面那层蜜糖甜丝丝的,瞬间冲淡了嘴里的苦涩。
“还装睡?”清冷的嗓音带着几分笑意。
梁十七手指颤了颤,不愿睁眼,大抵是人生病的时候总会有些矫情,也不知道杨鸿云戳到了她哪根柔.软的神经,泪珠不争气地顺着眼角没入了鬓发。
杨鸿云心头蓦地一软,用手指拭去她眼角的泪花,放缓了语气道:“怎么还哭上了?”
梁十七脑袋一偏,就是不理他。
杨鸿云无奈,只得替她掖好被子,到外屋对杨松和卢翠桃说道:“爹,你们先回去吧,免得让娘担心,我留下来照顾十七。”
“好。”杨松虽然有很多话想跟儿子说,但也知道眼下不是好时机,知道杨鸿云被放出来后,他心里便踏实了,其他的等以后再说吧。
卢翠桃一个黄花大闺女也不宜在外头过夜,她把药留下,嘱咐杨鸿云道:“徐大夫说两个时辰喝一次药,直到十七的热症退下去才能停,一贴药能熬两碗,外头的药炉子里还有一半。”
“好,多谢。”杨鸿云一一记下。
“不用,不用。”卢翠桃有些紧张地摆摆手,她还是第一次和杨鸿云说上话,不知为何,她觉得杨鸿云盯着她的时候有点骇人。
她不敢久留,低头跟着杨松出去了。
徐大夫没睡饱,感觉十分困顿,便去后院小憩,让杨鸿云有事再找他,潜意思就是:没事就别来烦老子!
杨鸿云应下,回屋见梁十七撑着手臂坐起,赶忙过去扶她:“你还病着,起来作甚?”
“想喝水。”梁十七捂着额头吸了吸鼻子,感觉有些头重脚轻,声音沙哑道:“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说要等张大人明日回来再做审.判?”
杨鸿云倒来温热的开水,递到她唇边轻声解释道:“张大人收到子桓的书信,筵席结束后连夜快马加鞭赶回,有崔家作保,他自然就将我放了。”
梁十七点点头,没有多加怀疑。
古人阶级观念很重,在权势面前,人命算不得什么,杨鸿云背靠金陵崔家这座大山,他的命可比一个小混混要来得重要。
梁十七虽然不赞同这种思想,但她也不会傻到用现代的三观去对抗这个世界。
就着杨鸿云的手喝了半杯水,梁十七干涸到冒烟的嗓子总算舒服了些,她精神不济,跟杨鸿云说了两句话后又睡了过去。
杨鸿云替她掖了掖背角,走出药馆看到石阶外停着一辆精致的马车,车前木牌垂落,上头雕刻着一个朱红大字:崔。
他朝着马车走去,伸手屈指在车壁上敲了三下。
里头的人撩起布帘子,露出一张憔悴苍白的面容来:“你今晚不回去?”
杨鸿云摇头:“十七热症未散,等明早再走。”
崔桓朝小厮招招手:“去府上取支人参来。”
“不用了。”杨鸿云叫住小厮,想了想又说道:“帮我准备明早的马车。”
“是。”小厮快步回府,对杨鸿云的态度很是恭敬。
崔桓闻言璨然一笑:“你可算是不把崔府当外人了,怕不是明早太阳要打从西边出来。”
杨鸿云神情淡淡,对他的态度,和对崔钰时的态度完全不同。
崔桓对杨鸿云的反应见怪不怪,哂笑道:“你说,如果当年没有祖父阻拦,你我,又是何况景?”
杨鸿云目光悠远,像是在出神:“大概是死了吧。”
“呵,咳咳......”崔桓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冷笑后便剧烈地咳嗽起来,本就苍白的脸色在夜幕中似乎变得更加透明了些。
杨鸿云就这么站在马车旁,看崔桓的眼神算不上冷漠,但也没多少温度,更多的是疑惑,他问:“你是真病还是假病?”
崔桓用帕子抹了把嘴角,气浮虚弱,眉眼间笑得有几分凉薄:“时间太久,假的也变成真的了,就如同你一样,不是吗?”
杨鸿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回药馆里去了。
崔桓坐在马车里,隐隐还听到杨鸿云跨进门槛时嘀嘀咕咕说了一句:“几年过去,戏还是那么多,真是吃的空出来跟你聊天。”
崔桓:“......”
他娘的,又被嘲讽了。
这人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那么讨厌!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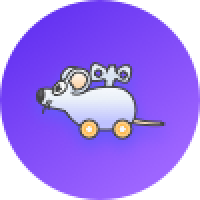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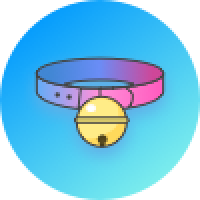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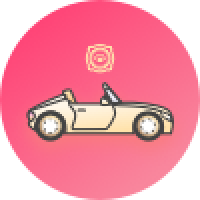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