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6章
此是常如意的计策失败了么?
那她,那她可咋办?!
会不会暴露她在里头参了一脚?!
不——这全都是小事儿,莫非,她真真地要在几今后出府,嫁给那自己并不爱的汉子,便那样灰头土脸的过一生么?
一刹那间,春云的面色全都有一些惨白。
鹦哥抬首,不经意恰好看着了春云的面色。
亦是春云有一些失魂落魄,一刹那间忘记了收敛掩匿。
鹦哥心里边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
常如意这般,同春云何干,她咋这样一副面色?
鹦哥突地便想起一桩事儿,常如意落水,三少是咋晓得的?
是偶然碰见的,还是,有人去通风报信啦?
鹦哥心头沉了下,起了身。
鹦哥这忽然的举动,要恰在走神的春云骤然吓一大跳,面色有一些惨败的看向鹦哥。
只是一个起来,居然可以吓成这般,不是心虚又是啥?......鹦哥心里边愈发沉重了。
春云掩匿般的笑着垂下头去:“恰在想事儿呢,反而是给你举动给惊着了。”
鹦哥笑道:“是我太莽撞了。”顿了一下,又道,“忽然想起了主儿嘱咐的一桩事儿我还没作呢,春云你先歇息着,我过去瞧瞧。”
春云心里边正忙乱着,哪儿听的出鹦哥话中头的漏洞?
鹦哥历来是水莲堂头一个妥帖人,咋会没完成主儿的嘱咐便过来茶汤间休憩啦?
春云却是没寻思到这一些,心烦意乱的点了下头。
鹦哥心里边愈发沉重了,仅是面上愈发不动音色。
她在走出茶汤间起先,心头不忍,转脸抚着门框,瞧了春云一眼,轻声道:“春云,咱四个打小便在府中头一块长大,你还记的青梨么?”
春云的面色刹那间便惨白一片。
青梨,她咋会不记的?
鹦哥青梨春云秋霞,她们四个,曾经是整个祁山郡公府中最为要人艳羡的四朵姊妹花。
然却,青梨却是起了不应当起的心思,她见次房言二太爷那一只有一个病恹恹的嫡子,没准啥时候便去了,届时倘若是她可以生下儿子,必定是整个次房实际的女主人。即使再不济,生个闺女,那亦是次屋中头的独一分呀......
青梨想去爬言二太爷的炕。
仅是这桩事儿青梨还没成功,便令言三少给撞破了。
老太过大怒,丫环想当爷的姨太,这无可厚非,可丫环却是想用一些下作手腕,通过给主儿下药来爬炕,这便是其心可诛了。
即使是最为慈蔼宽跟的老太太,也是没法忍受青梨这般,这等因此背主了。
因此祁山太君径直要人打了下柳10板子,把人撵出了祁山郡公府。
说一句良心话,10板子加逐出府门儿,这可以说是非常轻的惩戒了。
仅是青梨是个没福分的,她出府后没多长时候,便给哥哥嫂嫂又提脚卖掉了换了银钱。这回她大约是没了好运气再碰见一回老太太那般慈蔼的主儿。她到了新主家,照旧是想爬太爷的炕,给当家主母径直要人给扒了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活活打板子揍死了。
青梨的境遇,当初的那一些丫环们,一向引觉得戒。
现下鹦哥忽然又提起青梨,是否是她晓得了啥?
春云的心脏全都快跳出嗓子了。
不对,不可能。她啥也是没作!她仅是见安娘子这客人落水,奔去通知了三少而已......
这压根便不算背叛主儿!
春云强行令自己沉静下来,面上扯出一个笑来:“好端端的,鹦哥你提青梨干啥?”
鹦哥仔细瞧了瞧春云那瞧上去没啥,实际却是慌张到手脚全都僵直了的样子。
她心里边叹了口气儿。
同为水莲堂的大丫环这样经年,她适才的提醒,也是算作是尽了这分情谊了。
盼望这桩事儿,跟春云真真地没啥关系。
鹦哥径直去啦言宾贤养伤的阁间那儿。
言宾贤自打从常如意的阁间里头回来,不知怎地,意志便有一些消沉,急的侍奉的家丁团团乱转,又不敢扰了主儿,不要提多难遭了。
鹦哥这般过来,便像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家丁险些便给鹦哥跪了。
家丁殷勤的为鹦哥打着竹帘,引了鹦哥进去,满是笑的恭维道:“鹦哥娘子一来,房屋中全都亮堂了许多。”
这实际上有一些不大中听了。
究竟房屋中头还躺着个主儿呢。
鹦哥也是没跟这一些不通文墨的家丁们一般计较。她自然大方的向言宾贤行了礼:“婢子见着过三少。”
言宾贤躺在炕上,眼皮也是没抬一下:“是奶奶要你过来的?”
鹦哥轻声道:“是婢子自己有事儿想问一下三少。”
言宾贤晓得鹦哥是水莲堂最为的脸的大丫环,是个非常妥帖的,她说有事儿,那定然不是啥小事儿。
言宾贤轻轻抬眼:“啥事儿?”
鹦哥轻轻咬了下下唇:“敢问三少,你那时去救安娘子,是有人报信还是偶遇?”
言宾贤并非是个笨的,他见鹦哥忽然问起了这,目光轻轻一狭,又想起那诡异的分明是胡春姐,救上来却是变作了常如意的事儿,眼睛又沉了二分。
他凝声道:“何至于有此问?”
现下无凭无据,不可以仅凭借着春云的失常,便判定她有毛病,鹦哥便没说,仅道:“有几点疑问,婢子还是不敢铁定,不可以讲出来毁人名誉,还望三少见谅。”
言宾贤常去水莲堂,跟鹦哥也是算打过许多回交道了。他晓得鹦哥的为人,倘若不妥帖,她必定是不会张口的。虽自己身为主儿可以威逼她,可这般有啥意思?
言宾贤垂下眼睛,淡声道:“是春云过来同我道,安娘子落水了......这又怎样?”
鹦哥全身一震,果真是春云去报的信!
春云跟这件事儿,是否是真真地有啥牵连?!
鹦哥不敢相信。
言宾贤见鹦哥这幅样子,心知这必定是春云出了啥不妥的地方。
他心头一动,鹦哥历来是个嘴紧的,否则亦是不会当了奶奶心腹这样经年。他心头那困惑,何不径直跟她说,没准儿有啥意外结果呢?
言宾贤是个杀伐果决的,起了念头,轻轻考量一通后便径直开了口:“有桩奇事儿,反而是也恰好同你说一说。”
鹦哥全身一凛。
她神情变的有一些凝重,向言宾贤参礼:“三少请讲。”
言宾贤垂着眼,似是有一些漫不经心道:“实际上亦不是啥大事儿,仅是这桩事儿挂在心头,终究不大舒坦罢了。”他顿了一下,见鹦哥神情郑重,心里边反而是非常满意,沉着的继续道,“起先我在房屋中,春云跑来同我说,安娘子落水了。我寻思着总是表兄妹一场,便过去一瞧。谁晓得池子中头沉浮的压根不是常如意,而是......”
言宾贤顿了一下,终是没把胡春姐的名儿讲出来。
他囫囵的以“旁人”取代过,又飞疾道,“我救了那旁人后,便晕倒了,岂知醒来后,你们全都跟我说,我救的是常如意。现下看起来,我着实是救了她,可为啥,那时我居然把常如意当作了旁人?”
鹦哥有一些骇大了眼。
她晓得三少是习武的,眼神如炬,又同常如意相熟,定然不会有啥“认错人”一说;然却诡异的是,认错人的状况真真地出现了。
那般也便是说,有啥在影响着三少的认知,要他的判断产生了错误?
鹦哥好长时间没讲话。
半日,她才开了口:“三少,你救安娘子时,许多丫环婆娘全都在场,因而,你救的人必定是安娘子没错。至于你为啥把安娘子当作了旁人救上......婢子驽钝,反而是想不明白了。”
言宾贤听了亦是不灰心失望,他本来便没指望这丫环可以给他解惑。
他淡淡的点了下头,便令鹦哥下去。
岂知,历来妥帖听话的鹦哥,却是寸步未动。
面上,满当当全都是趔趄挣扎跟犹疑。
言宾贤心头一动,亦是不催促鹦哥。
他晓得,像鹦哥这般的妥帖丫环,会想明白的。
果不其然,过了半日,鹦哥才垂着头轻声道:“仅是有一丁点,非常可疑。”
言宾贤道:“你讲。”
鹦哥轻轻咬了下下唇,至此才道:“是春云......为啥安娘子落水,她先跑来寻三少?”
仅是简短一句,言宾贤的目光却是一亮。
是了,虽说那时他隔的那冰湖非常近,可出了事儿,首先应当是寻人救人,而春云,不去寻那一些身强力壮倚靠近冰湖的家丁婆娘,而是径直跑来告知了他......
即使是要回禀主儿,春云莫非不应当回禀的是老太太么?!
倘若怕老太太担忧,那也应当是同大丫环鹦哥商议呀,就这般贸冒然跑来寻了他——
倘若是后边没出那桩奇事儿,这事儿也便罢了,究竟虽讲不大过去,亦是不算啥问题。
可独独后边出了那桩事儿。
独独是他,把常如意认作了胡春姐。
独独是他,萧山伯府现下哭着闹着要把常如意嫁给他,常如意乃至以死相逼......
这一串讯息在言宾贤头脑中略过。
言宾贤眼睛愈发深沉了。
......
鹦哥回至水莲堂时,天色有一些晚了。
春云不知是否是心虚,一向在茶汤间门边张望,瞧着鹦哥面色如常的孤自一人回来,居然是一副松了好大一口气儿的样子。
鹦哥心里边愈发难过。
她面上却是照旧如往常般。
小丫环嘁嘁喳喳的迎上,逢迎鹦哥道:“鹦哥姐姐,老太太本能的问了你好几回,才发觉今日下午你是歇班的......”
鹦哥冲着小丫环点了下头,掀了竹帘,在外间里过了过寒气,至此才朝老太太的内阁行去。
祁山太君见着鹦哥反而是开心异常,招呼着她过去,提起了胡春姐嫁妆的事儿:“......今日见十三王爷过来谈小定的事儿,我倒想起一件旧物来。起先我小定那片刻,老郡公爷送了我一块白玉雕成的大雁,我记的一向收在库房中。你可晓得搁在哪儿啦?”
鹦哥掌管着祁山太君私库的钥匙,每年全都再清点一遍老太太的私库。她仅稍作一想,便回忆起来,笑道:“婢子记的呢,那白玉大雁一向搁在金缂丝楠木屉中头。便搁在丙号屉中收着呢。”
祁山太君便满意的点了下头,叮嘱道:“转脸把这白玉大雁也是给春儿添到嫁妆上去。”
鹦哥脆生生的应了。
祁山太君便想起桩啥事儿,屏退了左右侍奉的丫环,便留下鹦哥一个,笑狭狭的要鹦哥再近前一些:“......提起来,起先便同你讲过,待春儿成婚时,你跟过去作个屋中的掌事小娘子......”
鹦哥历来全都是温绵笑着的面上头一回出现了惊惶失色的神情,她噗嗵一下跪下,有一些惶惶然:“老太太,是婢子哪儿出错了么?”
历来端庄稳重的鹦哥,泪水全都快淌出来了。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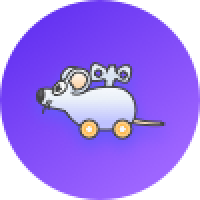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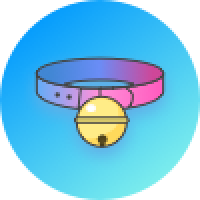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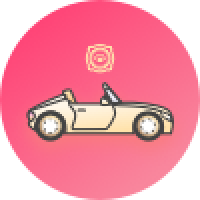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