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7章
“问这样多,自然而然是为三叔着想。”
胡春姐声响轻轻柔柔的,面上的笑也柔的像三月的风,可胡姜氏无端便觉的,自己这孙女儿笑的冷咻咻的,怪瘆人的。
再讲了,她会这样好心为她三叔着想?胡姜氏狐疑异常,在她心头,她这大孙女儿便是个阴险狡诈的主,她讲的话,非常多时候全都是个坑。
胡禄宗却是一喜,还觉得自己这侄女儿大约是想通了,喜滋滋的:“春姐,我可讲了,我是真诚纳鹦哥为妾的,后边儿定然委曲不了她!不便是个丫环嘛,咱一家人,还用这样外道!”
胡春姐轻笑一下:“三叔,你这刚从乡间来帝都,却是不知了。”
胡禄宗给胡春姐那轻飘飘的目光给一激,满口道:“我有啥不清楚的?帝都的规矩比乡间大我是晓得的,其它的还是有啥?大家不全都是用嘴儿吃饭的?!”
他讲异常大音。
一般而言,愈是心虚,便愈要用声响来掩匿。
胡春姐一笑。
仅是笑颜没达到瞳孔深处。
胡春姐随便指了一下外边:“三叔来时可见着外边撒扫的粗使丫环啦?”
祁山郡公府家大业大,平日中维持各院儿清洁卫生的丫环婆娘家丁可非个小数。
胡禄宗有一些纳焖,同时也黯黯提防,唯怕阴险狡诈的胡春姐再把他给带到坑里去。
寻思到这,胡禄宗又是有一些气焖。
他们村落中的,提及胡春姐这有能干有出息的,全都免不了会明里暗中笑话胡家人一家人。笑话他们没眼力劲儿,胡春姐那般能干的,倘若是好生相处,不讲其它的,便说凭借着亲爷亲奶的身分,胡家人咋会少了好处?
偏生这胡家人便是作!
生生的把这血缘亲情全都给作没啦!
如今村落里谈起胡家人前一些年对次房那几个娃作的那一些事儿,全都禁不住摇了下头。
胡禄宗瓮声瓮气道:“见着了又咋啦!”
胡春姐随便道:“那一些在外边撒扫的粗使丫环,到了年岁,府中头全都会尊重她们的意见,乐意出去嫁人的,给笔银钱要她们出去自行婚嫁了。”胡春姐顿了一下,目光在胡禄宗身体上绕了一圈儿,意味深长道,“便那等粗使丫环,出去自行婚嫁,多半配的全都是家里边小有薄产品行俱佳的儿郎。”
这“小有薄产”“品行俱佳”,不管哪儿个词,全都像是在直直的往胡禄宗面上扇巴掌。
祁山郡公府的人不清楚,胡家的人自己还是不清楚么?
便胡禄宗那日天游手好闲无所事儿事儿还生性好赌的,可以跟那俩词哪儿有个粘边儿?
胡禄宗的脸涨红了下。
不是羞的,是气的。
他气胡春姐居然这样不给他脸面!
胡姜氏见儿子发窘,非常不耐心烦道:“你三叔咋亦是你三叔,外边那一些人怎样跟他比!不便是个使唤的丫环!”
这意思实际上便有一些无赖了。
——你三叔再咋不可以全都是你三叔!有这一层关系在这儿,他便比外边那一些人高贵上百倍!
胡春姐历来非常厌憎胡姜氏这副永永远远理所应当的吸血样子。
她凉凉嗤笑,没理睬胡姜氏,亦是不管胡禄宗忿恨的瞠着她,施施然继续道:“倘若是三叔觉的外边粗使丫环这例子不大好,我们便来说一说这二等丫环的分例。”
胡春姐顿了一下,扬声叫了“金瑚”。
金瑚是水莲堂中头的一个二等丫环,在丫环里头年岁不大不小,翻过这年来适才好16。
她们家里头爷娘亲全都是祁山郡公府中有头有脸的掌事,勤勤恳恳为祁山郡公府干了几十年,家里边的几个死小子也是在府中头各处当着差。
她父亲她娘亲任劳任怨干了大半生,临老了给最为宠爱的小闺女求了个恩典,求府中头把她的身契发还。
由于金瑚小时候的青莓竹马,中了下人,亲身过来下聘求娶金瑚过去作当家太太。
老太太问过金瑚后,当场便允了。现下金瑚同大丫环中的春云一般,虽还是在水莲堂侍奉,可大部分时候全都是在房屋中绣嫁妆,待过完这年,便要把她们嫁出去了。
胡春姐特特点了金瑚出来,金瑚是个机灵的,多少能猜到二分表娘子叫她作啥。
她笑狭狭的出来,福了福身体:“给老太太,二位表娘子请安。”
祁山太君年岁大了,便爱看些团团圆圆的事儿,金瑚这桩婚事儿是件挺好的,她看见金瑚也开心异常。
胡春姐随便道:“金瑚,同我这边儿的亲戚,好生说一说,你嫁的是啥人家。”
金瑚便带着羞意的笑起:“娘子说笑了,婢子嫁了个举人,亦是不算顶好。府中头好些大姐小妹全都比婢子强,自然而然也是会嫁的比婢子好。”
举人!
胡家人的身体全都震了震。
实际上,他们对举人是个咋样的阶级全都不大清晰,可挡不住家里边有个苦读经年的胡海城,由于种种缘因,到如今还没考上秀才。
在胡家人眼中,秀才便已是顶顶难考,顶顶厉害的了。
哪家里边出了个秀才,便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儿。
现下一听闻祁山郡公府中的丫环居然随意便嫁了个举人,还是嫁的不算顶好,即刻眼球全都快从眼圈里掉下来了。
这一家的丫环,这样厉害的么!
胡家人有一些瑟缩发抖了。
一边一向看好戏没讲话的言宾贤轻轻勾了下唇瓣儿。
胡禄宗眼瞧着垂着头的鹦哥,那婀娜多姿的身段,莹白如玉的肌肤,心头一荡,还是有一些不甘心,指了一下鹦哥:“莫非她亦是个要嫁举人太爷的?!”
这话一问,胡禄宗便看着边儿上许多丫环全都矜持的抿唇一笑。
胡禄宗几近即刻明白,他闹笑话了。
这鹦哥的品级,没准儿比那叫啥金瑚的还是要高......
这样一想,胡禄宗心里边翻江倒海的不舒坦。
竹帘后边的宴席室中,许多丫环全都在那黯搓搓的竖着耳朵听。
春云本在那绣嫁妆,可自打隔着竹帘见了那个人进了房屋后,春云的心思便飞了一半儿出去。
一同绣嫁妆的金瑚给叫出,春云飞针走线的手掌便是一顿,险些扎出血来。
她心里边讲不出啥感受。
春云晓得胡春姐此是在借丫环的口舌告诉胡禄宗他想娶鹦哥那是痴心妄想。
现下这水莲堂中头,订了亲的丫环实际上还是有几个的,可最为有身分的,金瑚算一个,她春云算另一个。
这叫了金瑚出去,料来接下去便应当叫她了。
春云既盼看着片刻表娘子能把她叫出去,要她瞧一瞧那给她搁在内心深处之人的模样;又是有一些祈祷表娘子不要叫到她。
在那个人跟前,她不乐意说自己即要嫁给另外一个汉子。
春云犹疑的怔忡了好片刻,手掌上的针更是凶悍扎了几下指头头,洇出来的血粘染到绣布上,这任劳任怨绣了大半日的玩意儿即使作是白忙了。
然却春云犹疑了好一阵,亦是不见胡春姐叫她。
她便明白,大约是用不到她出去了。
春云又是松了一口气儿,又是怅惘异常。
心里边有个念头却是清晰异常:过了上元节,她便要给嫁出府去了,在那起先,瞧起来她要想法儿联系下安娘子了......
水莲堂正厅中,胡春姐笑嘻嘻的瞧着额上红筋全都显出来的胡禄宗:“三叔,你只怕不知,鹦哥乃是整个水莲堂中头最为有体面的一等大丫环。”
她虽没直说,话中话外意思已表达够了。
你算啥东西?
连外边粗使丫环嫁人全都不会考量你这类的,还想舔着个脸求娶人家一等大丫环?!
胡姜氏捉摸了下,算作是回过胡春姐话中头的味来,即刻便怒了:“胡春姐,你这是啥意思,此是在埋汰你三叔,觉的你三叔配不上一个丫环?!”
老胡头也蛮不开心。
在他看起来,胡春姐起先跟家里边拧了一些,可好赖是他老胡家的种,没他老胡家,便没胡春姐那姊弟仨。
不管咋说,胡春姐全都的念着家里边的不易,帮衬帮衬家里边。
特别是如今,胡春姐姊弟仨跃上枝儿头草鸡变金凤了,居然仅寻思着她们自己,一丁点全都不寻思着帮一帮家里头人。
现下无非是给老三讨个丫环当个妾,就这般说这道那的,倘若后边他们真有事儿寻到了胡春姐身体上,那不是还的好生给他们面色看?!
老胡头重重的咳了下:“我说春丫头,只是个丫环,再咋金贵,亦是你姥姥家的仆人!”
这便是要以孝道压胡春姐了。
胡春姐完全恼了,拿她姥姥说事儿?
她甜甜的笑道:“爷,你这不挺明白嘛,这是我姥姥府中头非常的脸的大丫环,我便想问一下了,某些人哪儿来的大脸,张口便要人家去给你那不成器的儿子当妾氏!亦是不照照铜镜瞧瞧自己啥德性,配不配的上人家!”
胡春姐笑的比三月梨花还是要潋滟,讲出来的话却是要胡家人刹那间全都给气炸啦!
言宾贤似是头一回见着胡春姐这一面,目光落在胡春姐面上时,情不自禁的轻轻顿了一顿。
算了......言宾贤心头哂笑,他此是在干啥,表妹全都已由圣上下啦旨指给了十三王殿下,他应当收起所有不应当又的心思,仅把这小娘子单纯的当作表妹来痛。
胡春姐的话听在胡家人耳朵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胡姜氏气炸了,在那指着胡春姐,把乡间那一套污七秽八的骂人话搬来过来,放炮一般一缕脑皆都冲着胡春姐骂去。
胡春姐亦是不讲话,仅敛了笑,凉凉的瞧着胡姜氏。
祁山太君没嫁人前是把门贵女,嫁人后先是冢妇,再便是取了中馈的掌家太太,便是偶然撞见底下家丁婆娘混不咎的相互骂,全都没骂的这样难听的。
乃至这胡姜氏骂上头来,便像起先那般,还杂了几句骂胡春姐已逝生母孟苏娘的下贱话。
祁山太君本来又是大诧又是心痛,她痛到了心尖上的外孙女儿,在乡间那般经年来,过的居然是这般的生活?
再一听胡姜氏连孟苏娘的骂上了,祁山太君心痛的一刹那脸全都白了。
她的闺女......她娇养了十经年的闺女,半句重话全都舍不的讲的闺女,在胡姜氏口中,居然形同猪狗!
可想而知她的闺女为啥年岁轻轻便早早的逝去啦!
几近在祁山太君面色为之一变的那刻,胡春姐便发觉了姥姥的异常,她紧忙冲来,抚着祁山太君,心急道:“姥姥,你消消气儿!”
祁山太君面色由白转红,喘不上气来。
言宾贤也冲来。
胡春姐急的转头便是大吃婆娘:“把她嘴给我堵上!”
婆娘早便看那胡姜氏不爽了,现下主儿下啦命,几个婆娘即刻冲上上,胳膊腿脚利索的把胡姜氏一捆,再熟稔的往胡姜氏口中头塞了块帕子儿。
胡家人全都给这变故惊呆了。
待反应过来,老胡头还在那没说啥,胡禄宗便冲上,嚷嚷道:“你们此是想干啥!快放开我娘亲!”
胡春姐转头便是一吃:“给我住口!”
那股凛然的气势,要胡禄宗呆了下,居然一时候老实下来。
胡禄宗一瞧好像惹出了大事儿,亦是不敢再去嚷嚷给胡姜氏解绑。
胡春姐发觉的早,又一通给祁山太君顺气,祁山太君可算作是缓来。
祁山太君活了这样一大把年岁,也见着过许多腌臜事儿,可像胡姜氏这般拿着她最为最为心爱的闺女外孙女儿来肆意辱骂的,她还是头一回碰着。即使祁山太君在见胡姜氏起先心里边早已有了心理预备,觉的这胡姜氏可可非个慈蔼的婆母、奶。
可祁山太君是真真地没寻思到这胡姜氏能泼辣成这般!
一寻思到闺女跟几个外孙这一些年来吃的苦,祁山太君心里边便心如刀割,老泪纵横。
外孙女儿她还可以弥补一二,可她那如珠似玉的闺女,却是再也回不来了。
祁山太君的丧女之疼,似是给人揭开了伤疤,心里边痛的针扎一把,密密麻麻的,脑袋上全都出了一圈汗。
 爱心猫粮1金币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南瓜喵1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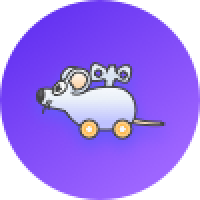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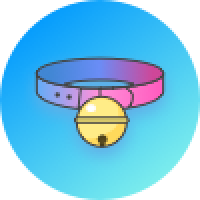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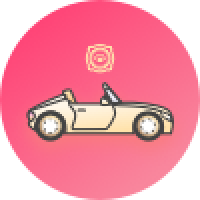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

